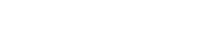第一次走进叔叔婶婶的家,谢南风非常不自在。
自己不过是空有一副成年人的外表,命运还是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17岁的他,独自一人离开法县,投靠沈市这位从未谋面的叔叔谢子临,开始他孤独的异乡生活。
说寄人篱下有点不妥,他从没想到自己这个从未谋面的叔叔和婶婶,对这个从天而降的他,竟然如此的热情。
自己平时都是住校,只有周末回来,平时开个家长会叔叔自然是要去的,与老师的沟通交流也是有的,学习也是要过问的,馆子要下的,衣服鞋子也是要买的。
也许叔叔努力想尽他作为叔叔的责任,但是婶婶就不一样了,按理来说一般意义上婶婶都是外人,又怎会有多么亲密可言,能做到客客气气,就已经是好人了。
也许是因为叔叔婶婶没有孩子,谢南风的到来着实让谢子临和孟非飞忙活一番,给他布置房间,准备物品的过程犹如要迎接一个新生儿的到来。
在选购物品的时候孟非飞很是欢喜,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感充盈着她的身体,虽然没见到这个侄儿,但是她已经欢喜了。
准确来说是她对一种新鲜事物的欢喜。
跟谢子临在一起这些年,一直没有孩子,虽然他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一定要有个孩子的人,起码看上去他们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那种夫妻,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,不是他们的调子。
但很多事情都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,可是人们往往就是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,透过表象看本质总归是辛苦的,麻烦的。
曾经为了要孩子所走过的心酸历程遥远而陌生,而现在就要有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大小伙子来到他们身边,一种冥冥中注定般的感觉。
起码孟非飞是激动的,可也是乱的。
孟非飞给谢南风准备了很多东西,洗漱用品都是男生用的好货,舒适的睡衣套装和质量特别好的拖鞋。
在这过程中她了解关于谢南风的基本信息。身高体重多大的脚,这是一个非常高标准青春年华的尺寸。
但对于谢南风来说,不管是沈市中学,还是叔叔的家,他都很难很快适应。
自己就这样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裹挟着走到了这里,一切都不由得他做主,他也做不了主,他连想都没想过就把自己交了出去。
本来平静朴素的日子,在一个多月前的中午戛然而止。
谢南风正在教室里面靠窗的位置,趴在桌子上望着一棵茂密的丁香树,他觉的丁香花特别不像花,不像花的丁香花默默的陪伴着他。
丁香花的味道成了他对法县唯一的理解,在以后的日子里,他只有看到丁香花,才能想起法县,而其他关于法县的回忆,他都忘了,一种主动的忘记。
满眼的淡紫色,在强光下模糊成一片如海洋般的淡紫色,他浑然不知地,好像自己正在悄悄地,走进那片淡紫色的海洋中去了。
真奇怪,一棵丁香树竟然变成了一片海。
正望地出神的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,让他坐下来说:“你妈妈现在医院里,你不要担心,现在我陪你一起过去。”
妈妈乘坐的小巴车,撞上了一辆大卡车,车上的人几乎都走了。那天早上起来妈妈给他准备好早点:“今天我给你姥姥上坟去。”
“我也要去,等周末一起。”谢南风说。
“算了,你现在学习紧张,今天天气好,不能再拖了。”
每年丁香花开的时候都是如此,只是具体时间不一定,那条路走了多少年没有任何问题,往年谢南风都是要陪着妈妈一起去的。
姥姥从小把他带大,他知道这份感情。姥姥走了以后,每年去她的墓地上待上一会儿,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很欣慰,很踏实。
他一直觉的姥姥的坟前应该有棵丁香花。
姥姥走的那一年他才七岁,对死亡的了解还不清晰,可是对于姥姥的感情倒是清晰的。
姥姥的背是他呆过的最安全和温暖的地方。在法县强烈的太阳光下面,姥姥的背如同一辆舒适无比的轿子,托着他走过每一条街巷。
一路上总是被各种别的姥姥们嘲笑:这么大了,还要背!
可是姥姥从来没有对他说过:这么大了还要背。
五岁了,背起来的时候他的腿已经到了姥姥的膝盖下面,可是姥姥还是要背着她,这时候已经不是他需要姥姥的背了,而是姥姥的背需要他。
祖孙俩的幸福在这一背一落之间潮起潮落,自在吉祥。
那是一种不需要任何人去理解和接受的关系,姥姥可以把他所有的能量和情绪,稳稳地接在背上,而他也稳稳的知道姥姥稳稳地接住了他。
好像自己从一个很高的地方跳下,而丝毫没有恐惧感。
只是这样的关系和感受人世间太稀有了,以至于人们都在怀疑,怀疑姥姥宠坏了他。而姥姥和他都懂的,他爱她,她爱他。
在谢南风这十几年的人生道路中,他就没有叫过爸爸这两个字,小时候姥姥说过爸爸死了,再大一点他好像懂了一点,但是他也不再过问了。
他的生命里只有妈妈姥姥,就非常幸福了,这两个女人如太阳一般,把他的生活烤的暖呼呼的。唯一的遗憾就是姥姥走的太早了,剩下妈妈一个人的日子总归是难过。
姥姥的离开是突然的,突然到谢南风感觉不到。
七岁的他甚至哭都哭不出来,因为他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小伙伴那个新的玩具。姥姥死了这件事儿,没有新玩具那么有魅力。
他这样想其实是因为他知道,姥姥也是这样想的,只是他还小还不能把这感觉表达清楚。
姥姥死了,只是很久很久以后谢南风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。
有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恍惚发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:“你的工作的事我在想办法,有个稳定的工作我也放心了。南风中学了就让他去沈市上学去,到时候我来办这件事,你放心。”
妈妈的声音:“办这办那,你慢慢办,啥时候让孩子叫你一声爸?你以为他不知道吗?别看他小,心里啥都明白。”
“目前就这样,以后再说。”男人说。
“你以后别偷偷摸摸地过来了,我妈也不在了,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过来。”妈妈说。
“好,只要我想你了,就过来行吗?”男人说。
“滚犊子。”妈妈说。
自己不过是空有一副成年人的外表,命运还是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17岁的他,独自一人离开法县,投靠沈市这位从未谋面的叔叔谢子临,开始他孤独的异乡生活。
说寄人篱下有点不妥,他从没想到自己这个从未谋面的叔叔和婶婶,对这个从天而降的他,竟然如此的热情。
自己平时都是住校,只有周末回来,平时开个家长会叔叔自然是要去的,与老师的沟通交流也是有的,学习也是要过问的,馆子要下的,衣服鞋子也是要买的。
也许叔叔努力想尽他作为叔叔的责任,但是婶婶就不一样了,按理来说一般意义上婶婶都是外人,又怎会有多么亲密可言,能做到客客气气,就已经是好人了。
也许是因为叔叔婶婶没有孩子,谢南风的到来着实让谢子临和孟非飞忙活一番,给他布置房间,准备物品的过程犹如要迎接一个新生儿的到来。
在选购物品的时候孟非飞很是欢喜,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感充盈着她的身体,虽然没见到这个侄儿,但是她已经欢喜了。
准确来说是她对一种新鲜事物的欢喜。
跟谢子临在一起这些年,一直没有孩子,虽然他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一定要有个孩子的人,起码看上去他们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那种夫妻,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,不是他们的调子。
但很多事情都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,可是人们往往就是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,透过表象看本质总归是辛苦的,麻烦的。
曾经为了要孩子所走过的心酸历程遥远而陌生,而现在就要有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大小伙子来到他们身边,一种冥冥中注定般的感觉。
起码孟非飞是激动的,可也是乱的。
孟非飞给谢南风准备了很多东西,洗漱用品都是男生用的好货,舒适的睡衣套装和质量特别好的拖鞋。
在这过程中她了解关于谢南风的基本信息。身高体重多大的脚,这是一个非常高标准青春年华的尺寸。
但对于谢南风来说,不管是沈市中学,还是叔叔的家,他都很难很快适应。
自己就这样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裹挟着走到了这里,一切都不由得他做主,他也做不了主,他连想都没想过就把自己交了出去。
本来平静朴素的日子,在一个多月前的中午戛然而止。
谢南风正在教室里面靠窗的位置,趴在桌子上望着一棵茂密的丁香树,他觉的丁香花特别不像花,不像花的丁香花默默的陪伴着他。
丁香花的味道成了他对法县唯一的理解,在以后的日子里,他只有看到丁香花,才能想起法县,而其他关于法县的回忆,他都忘了,一种主动的忘记。
满眼的淡紫色,在强光下模糊成一片如海洋般的淡紫色,他浑然不知地,好像自己正在悄悄地,走进那片淡紫色的海洋中去了。
真奇怪,一棵丁香树竟然变成了一片海。
正望地出神的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,让他坐下来说:“你妈妈现在医院里,你不要担心,现在我陪你一起过去。”
妈妈乘坐的小巴车,撞上了一辆大卡车,车上的人几乎都走了。那天早上起来妈妈给他准备好早点:“今天我给你姥姥上坟去。”
“我也要去,等周末一起。”谢南风说。
“算了,你现在学习紧张,今天天气好,不能再拖了。”
每年丁香花开的时候都是如此,只是具体时间不一定,那条路走了多少年没有任何问题,往年谢南风都是要陪着妈妈一起去的。
姥姥从小把他带大,他知道这份感情。姥姥走了以后,每年去她的墓地上待上一会儿,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很欣慰,很踏实。
他一直觉的姥姥的坟前应该有棵丁香花。
姥姥走的那一年他才七岁,对死亡的了解还不清晰,可是对于姥姥的感情倒是清晰的。
姥姥的背是他呆过的最安全和温暖的地方。在法县强烈的太阳光下面,姥姥的背如同一辆舒适无比的轿子,托着他走过每一条街巷。
一路上总是被各种别的姥姥们嘲笑:这么大了,还要背!
可是姥姥从来没有对他说过:这么大了还要背。
五岁了,背起来的时候他的腿已经到了姥姥的膝盖下面,可是姥姥还是要背着她,这时候已经不是他需要姥姥的背了,而是姥姥的背需要他。
祖孙俩的幸福在这一背一落之间潮起潮落,自在吉祥。
那是一种不需要任何人去理解和接受的关系,姥姥可以把他所有的能量和情绪,稳稳地接在背上,而他也稳稳的知道姥姥稳稳地接住了他。
好像自己从一个很高的地方跳下,而丝毫没有恐惧感。
只是这样的关系和感受人世间太稀有了,以至于人们都在怀疑,怀疑姥姥宠坏了他。而姥姥和他都懂的,他爱她,她爱他。
在谢南风这十几年的人生道路中,他就没有叫过爸爸这两个字,小时候姥姥说过爸爸死了,再大一点他好像懂了一点,但是他也不再过问了。
他的生命里只有妈妈姥姥,就非常幸福了,这两个女人如太阳一般,把他的生活烤的暖呼呼的。唯一的遗憾就是姥姥走的太早了,剩下妈妈一个人的日子总归是难过。
姥姥的离开是突然的,突然到谢南风感觉不到。
七岁的他甚至哭都哭不出来,因为他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小伙伴那个新的玩具。姥姥死了这件事儿,没有新玩具那么有魅力。
他这样想其实是因为他知道,姥姥也是这样想的,只是他还小还不能把这感觉表达清楚。
姥姥死了,只是很久很久以后谢南风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。
有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恍惚发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:“你的工作的事我在想办法,有个稳定的工作我也放心了。南风中学了就让他去沈市上学去,到时候我来办这件事,你放心。”
妈妈的声音:“办这办那,你慢慢办,啥时候让孩子叫你一声爸?你以为他不知道吗?别看他小,心里啥都明白。”
“目前就这样,以后再说。”男人说。
“你以后别偷偷摸摸地过来了,我妈也不在了,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过来。”妈妈说。
“好,只要我想你了,就过来行吗?”男人说。
“滚犊子。”妈妈说。